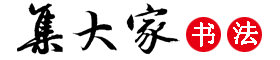却说菶如当日正接了一封俄国邮来的信件
却说菶如当日正接了一封俄国邮来的信件
上一句:
无上一句
下一句:
还没拆开
原文及意思:
《第十二回》
却说菶如当日正接了一封俄国邮来的信件,还没拆开,先见两个西装妇女的摄影,不解缘故。他夫人倒大动疑心起来。菶如连忙把信拆开,原来这封信还是去年腊月里,雯青初到圣彼得堡京城所寄的。信中并无别话,就告诉菶如几时由德动身,几时到俄。又说在德京,用重价购得一幅极秘密详细的中俄交界地图,自己又重加校勘,即日付印,印好后就要打发妥员赍送来京,呈送总理衙门存档,先托菶如妥为招呼等语,辞气非常得意。直到信末,另附一纸,说明这张摄影的来由,又是件旷世希逢的佳话。你道这摄影是谁呢?列位且休性急,让俺慢慢说来。
话说雯青驻节柏林,只等彩云觐见后就要赴俄;已经耽搁了一个多月,恰值德皇政体违和,外部总没回文。雯青心中很是焦闷,倒是彩云兴高采烈,到处应酬:今日某公爵夫人的跳舞,明日某大臣姑娘的茶会,朝游缔尔园,夜登兰姒馆,东来西往,煞是风光。彩云容貌本好,又喜修饰,生性聪明,巧得人意,倒弄得艳名大噪起来。偌大一个柏林城,几乎没个不知道傅彩云是中国第一个美人,都要见识见识,连铁血宰相的郁亨夫人,也来往过好几次。那郁亨夫人,替彩云又介绍认得了一位贵夫人,自称维亚太太,说是德国的世爵夫人,年纪不到五十许,体态虽十分端丽,神情却八面威风。那日一见彩云,就非常投契,从此也常常约会。不过约会的地方,不在花园,即在戏馆,从不叫登这夫人的邸第,夫人也没有来过。彩云有时提起登门造访的话,那太太总把别话支吾。彩云只得罢了。话且不表。
却说有一晚,彩云刚与这位太太在维良园看完了戏,独自回来,已在定更时候,坐着一辆华丽的轿式双马车,车上连一个女仆都不带,如飞地到了使馆门口停住。车夫拉开车门,彩云正要跨下,却见马路上有一个十七八岁的美童,飞奔地跑到车前,把肩膀凑近车门,口里还吁吁发喘。彩云就一手搭在他肩上,轻轻地跳了下来。进了馆门,就有一班管家们,都站了起来,喊道:“太太回来了,快掌灯伺候!”便有两个小童,各执一盏明角灯儿,在前引导。这当儿,那些丫鬟仆妇也都知道了,在楼上七跌八撞的跑了下来。那时彩云已到了升高机器小屋里,那些丫鬟仆妇都要上前搀扶,都道:“阿福哥,劳你驾了!让我们来搀着吧!”彩云冷笑了一声,自顾自仍扶着阿福。那机器就如飞地上升了。到了楼上,彩云有气没力的,全身都靠在阿福的身上,连喘带笑地迈到了自己卧房一张五彩洋锦的软榻上就倒下了,两颊绯晕,双眼粘饧,好象贵妃醉酒一般,歪着身,斜着眼,似笑不笑地望着阿福。阿福也笑瞇瞇地低着头,立在榻旁。彩云忽然把一个玉葱,咬着银牙,狠狠地直指到阿福额上,颤声道:“你这坏透顶的小子,我不想今儿个……”刚说到这里,那些丫鬟仆妇都从扶梯上走了进来,彩云就缩住了口,马上翻过脸来道:“你们这班使坏心的娼妇,都晓得这会儿我快回来了,倒一个个躲起来。幸亏阿福是个小子,不要紧,要是大汉子,臭男人,也叫我扶着走吗?”彩云说罢,那些丫鬟仆妇都面面相觑,不敢则声。阿福就趁势回道:“那辆车,明天还叫他来伺候吗?”彩云道:“明天有什么事?”阿福道:“怎么太太会忘了!刚才在路上,你不是告诉我,明儿个维亚太太约游缔尔园吗?”彩云想一想道:“不错,看戏的时候,她当面约定的。”说着,把眼瞪着阿福道:“可是我再不要坐轿式车了。明天早上,叫他来一辆亨斯美吧!”阿福笑道:“你自个儿拉缰吗?”彩云道:“谁耐烦自个儿拉,你难道折了手吗?”阿福笑了一笑,再要说话,听见房门外靴声橐橐,仆妇们忙喊道:“老爷进来了!”阿福顿时失色,慌慌张张想溜。彩云故意正色高声地喊道:“阿福,你别忙走呀!我还有话吩咐吗!”阿福会意,就垂着手,答应一声:“着!”“你告诉他,明儿早上八上钟来,别误了!”这当儿,雯青一头掀着门帘,一头嘴里咕噜着:“阿福老是这样冒冒失失、得风使篷的。”说着,已经踱了进来,冲着彩云道:“明天你又要上哪儿去了?”其时阿福得空,就捱身出房。彩云撅着嘴道:“到缔尔园去,会一个外国女朋友,你问她什么?难道你嫌我多出门吗?什么又不又的!”说着,赌气就一溜风走到床后去更衣洗面了。雯青讨了个没趣,低低说道:“彩云,你近来真变了相了,我一句话没有说了,你就生气了。我原是好意,你可知道今天外部已有回文,叫你后天就去觐见,在沙老顿布士宫Charlotenburg,离着柏林有二三十里地呢!我怕你连日累着,想要你歇息歇息呀!”彩云听了雯青这番软话,心里想想,到底有点过意不去,又晓得觐见在即,倒又欢喜起来,就笑嘻嘻走到床面前来道:“谁生气来?不过老爷也太顾怜我了。既然后天要觐见,明天早点回来,省得老爷不放心,好吗?”雯青道:“这也由你吧!”说罢,彼此一笑,同入罗帏。一宵无话。
次日清早,雯青尚在香梦迷离之际,彩云偷偷地抽身锦被,心里盘算出去的装束要格外新艳。忽然想起新购的一身华丽欧装,就叫小丫头取了出来,慢慢地走到梳妆台,对镜梳洗,调脂抹粉,不用细说。不一会,就拢上一束蟠云曼蟠髻,系上一条踠地綷察裙,颈围天鹅绒的领巾,肩披紫貂嵌的外套,头上戴了堆花雪羽帽,脚下踏着雕漆乌皮靴,颤巍巍胸际花球,光滟滟指头钻石,果然是蔷薇娘肖象,茶花女化身了。打扮刚完,自己把镜子照了又照,很觉得意。忽见镜子里面阿福笑嘻嘻地站在背后,低低道:“车来了。”彩云嗤地一笑道:“促狭鬼,倒吓人一跳!”随就把嘴儿指着床上,又附着阿福耳边,密密切切不知吩咐了些什么话。阿福笑着点头答应,就蹑手蹑脚地下楼去了。这里彩云收拾完备,轻轻走到床边,揭起帐子张了一张,就回声叫小丫头搀了一径下楼。到门口上车,打发小丫头们进去,又叫马夫坐在车后,自己就跳上亨斯美,轻提玉臂,紧勒丝缰,那匹马就得得地向前去了。走了一条街,却见那边候着个西装少年,远远招手儿。彩云笑一笑,把车放慢了,那少年就飞身上车,与彩云并肩坐下,把丝缰接了过来。一扬鞭,一摇铃,风驰电卷,向马龙车水中间滚滚而去。两人左顾右盼,俨然自命一对画中人了!不多会儿,到了缔尔园Tiergarten门前。
原来这座花园,古呢普提坊要算柏林市中第一个名胜之区,周围三四里,门前有一个新立的石柱,高三丈,周十围,顶立飞仙,全身金翅,是法、奥、丹三国战争时获得大炮铸成,号为“得胜铭”。园中马路,四通八达。崇楼杰阁,曲廊洞房,锦簇花团,云谲波诡,琪花瑶草,四时常开,珈馆酒楼,到处可坐。每日里钿车如水,裙屐如云,热闹异常。园中有座三层楼,画栋飞龙,雕盘承露,尤为全园之中心点。其最上一层有精舍四五,无不金釭衔壁,明月缀帷,榻护绣襦,地铺锦罽,为贵绅仕女登眺之所,寻常人不能攀跻。彩云每次到园,与诸贵女聚会,总在此间憩息。
这日马车进了园门,就一径到这楼下下车,阿福扶着,迤逦登楼。刚走到常坐的那一间门口,彩云一只纤趾正要跨进,忽听咳嗽一声,抬头一看,却见屋里一个雄赳赳的日耳曼少年,金发赫颜,丰采奕然,一身陆军装束,很是华丽。见了彩云,一双美而且秀的眼光,彷佛云际闪电,把彩云周身上下打了一个圈儿。彩云猛吃一惊,连忙缩脚退出。阿福指着道:“间壁有空房,我们到那里坐吧!”说罢,就掖了彩云径进那紧邻的一间精室。彩云坐下,就吩咐阿福道:“你到外边去候着,等维亚太太一到,就先来招呼。”阿福答应如飞而去。彩云独自在房,心里暗忖那个少年不知是谁,倒想不到外国人有如此美貌的!我们中国的潘安、宋玉,想当时就算有这样的丰神,断没有这般的英武。看他神情,见了我也非常留意,可见好色之心,中外是一样的了。彩云胡思乱想了一回,觉得心神恍惚,四肢软胎胎提不起来,就和身倒在一张红绒如意榻上,星眼惺松,似睡不睡的,正有点朦胧,忽听耳边有许多脚步声,连忙张开眼来,却见阿福领了一个中年妇人上来。彩云忙问阿福道:“这是谁?”阿福道:“这位就是维亚太太打发来的。”那妇人就接嘴道:“我们主人说,今天不来这里了,要请密细斯到我们家里去。主人特地叫我们来接的,马车已在外面等着。请密细斯上车吧!”彩云听了,想了一想道:“太太府上,我早该去请安,就为太太的住处不肯告诉我,就因循下来了。现在既然太太见招,我就坐我自己的车前去便了。”说着,回头叫阿福去套车。那妇人道:“我们主人吩咐,请密细斯就坐我们来车。因为我们主人的住处,不肯轻易叫人知道的。”彩云道:“这是什么道理?”那妇人笑道:“主人如此吩咐,其中缘故,奴辈哪里敢问呢?”彩云没法,只好叫阿福到身边,附耳说了两句话,阿福先去了,自己就立起身来道:“我们走吧!”那妇人在前,彩云在后,走下楼来。
刚到门口,彩云还没看清那车子的大小方圆,却被那妇人猛然一推,彩云身不由主被她推进车来,车门已硼的关上了,弄得彩云迷迷糊糊,又惊又吓。只见那车里四面糊着金绒,当前一悬明镜,两旁却放着绿色的布帘,遮着玻璃,一些望不见外面。对面却笑微微坐着那妇人,开口道:“密细斯休怪粗莽,这是主人怕你知道了路程,所以如此的。”彩云听了这话,更加狐疑,要问那妇人,又知道她不肯说实话的,心里不免突突跳个不住。正冥想间,那车忽然停了,车门欻的开了,那中年妇人先下车,后来搀彩云。刚跨下地,忽觉眼前一片光明,耀耀烁烁,眼睛也睁不开。好容易定睛一认,原来一辆朱轮绣幰的百宝宫车,端端正正地停在一座十色五光的玻璃宫台阶之下。那宫却是轮奂巍峨,矗云干汉。宫外浩荡荡,一片香泥细草的广场,遍围着郁郁苍苍的树木,点缀着几处名家雕石像,放射出万条异彩的喷水池。彩云不及细看,却被那妇人不由分说就扶上台阶,曲曲折折,走到一面大镜子面前,那妇人把镜子一推,却呀的一声开了,原来是个门儿。向里一望,只见是个窈窕洞房,满室奇光异彩,也不辨是金是玉,是花是绣,但觉眼光缭乱而已。就有几个华装女子听见门响,向外一望,问道:“来了吗?”那妇人道:“来了。”忽听嘤然一声,恍如凤鸣鹤唳,清越可听道:“快请进来。”那当儿,彩云已揭起了绣帏,踏上了锦毯,迎面袅袅婷婷的,来了个细腰长裙、锦装玉裹的中年贵妇,不用说就是维亚太太了。见了彩云,就抢上一步,紧握住彩云的双手,回头向那些女子说道:“这就是中国第一美女,金公使的夫人傅彩云呀!你们瞧着,我常说她是亚洲的姑娄巴、支那的马克尼。今儿个你们可开开眼儿了!”说完,就把彩云拉到了一张花磁面的圆桌上首坐下,自己朝南陪着。彩云此时迷迷糊糊,如在五里雾中,弄得不知所措,只是婉婉地说道:“贱妾蒲柳之姿,幸蒙太太见爱,今日登宝地,真是三生有幸了!只是太太的住处,为何如此秘密?还请明示,以启妾疑。”维亚太太笑道:“不瞒密细斯说,我平生有个癖见,以为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是两种人物,都是有龙跳虎踞的精神、颠干倒坤的手段,你道是什么呢?就是权诈的英雄与放诞的美人。英雄而不权诈,便是死英雄;美人而不放诞,就是泥美人。如今密细斯又美丽,又风流,真当得起‘放诞美人’四字。我正要你的风情韵致泻露在我的眼前,装满在我的心里,我就怕你一晓了我的身分地位,就把你的真趣艳情拘束住了,这就大非我要见你的本心了。”彩云不听这太太的话,心里倒还有点捉摸,如今听了这番议论,更胡涂了,又问道:“到底太太的身分、地位,能赐教吗?”那太太笑道:“你不用细问,到明日就会知道的。”说话间,有几个华装女子,来请早餐,维亚太太就邀彩云入餐室。原来餐室就在这室间壁,高华典贵,自不必说。坐定后,山珍海味,珍果醇醪,络绎不绝地上来。维亚太太殷勤劝进,彩云也只得极力周旋。酒至数巡,维亚太太立起身来,走到沿窗一座极大的风琴前,手抚玉徽,回顾彩云道:“密细斯精于音律吗?”彩云连说“不懂”。那太太就引弦扬吭地唱起来。歌曰:
美人来兮亚之南,风为御兮云为骖,微波渺渺不可接,但闻空际琼瑶音。吁嗟乎彩云!
美人来兮欧之西,惊鸿照海天龙迷,瑶台绰约下仙子,握手一笑心为低。吁嗟乎彩云!
山川渺渺月浩浩,五云殿阁琉璃晓,报道青鸾海上来,汝来慰我懮心捣。吁嗟乎彩云!
劝君酒,听我歌,我歌欢乐何其多!听我歌,劝君酒,雨复云翻在君手!愿君留影随我肩,人间天上仙乎仙!吁嗟乎彩云!
歌毕,就向彩云道:“千里之音,不足动听。只是末章所请愿的,不知密细斯肯俯允吗?”彩云原不懂文墨,幸而这回歌辞全用德语,所以彩云倒略解一二,就答道:“太太如此见爱,妾非木石,哪有不感激的哩。只是同太太并肩拍照,蒹葭倚玉,恐折薄福,意欲告辞,改日再遵命吧!”那太太道:“请密细斯放心,拍了照,我就遣车送你回去。现在写真镜已预备在草地上,我们走吧!”就亲亲热热携了彩云的手,一队高鬟窄袖的女侍前后呵护,慢慢走出房来,就走到刚才进来看见的那片草地上。早见有一群人簇拥着一具写真镜的匣子,离匣子三四丈地,建立一个铜盘,上面矗起一个喷水的机器,下面周围着白石砌成的小池。那水线自上垂下,在旭日光中如万颗明珠,随风咳吐,煞是好看。那太太就携了彩云,立在这石池旁边,只见那写真师正在那里对镜配光。彩云瞥眼看去,那写真师好象就是在萨克森船上见的那毕叶先生,心里不免动疑。想要动问,恰好那镜子已开,自己被镜光一闪,觉得眼花缭乱了好一回。等到捉定了神,那镜匣已收起,那一群人也不知去向了,却见一辆马车停在面前。维亚太太就执了彩云的手道:“今天倒叫密细斯受惊了。车子已备好,就此请登车,我们改日再叙吧!”彩云一听送她回去,很欢喜的,也道了谢,就跨进车来。车门随手就关上了,却见车帘仍旧放着,乌洞洞闷死人。那车一路走着,彩云一路猜想:这太太的行径,实在奇怪,到底是何等样人?为什么不叫我知道她的底里呢?那毕叶先生怎么也认得她、替她拍照呢?想来想去,再想不出些道理来。还在呆呆地揣摩,只见门豁然开朗,原来已到了使馆门口。彩云就自己下了车,刚要发放车夫,谁知那车夫飞身跳上高座,加紧一鞭,逃也似地直奔前路,眨眼就不见了。彩云倒吃了一惊,立在门口呆呆地望着,直到馆中看门的看见,方惊动了里边的丫鬟们,出来扶了进去。阿福也上前来探问,彩云含糊应了。后来见了雯青,也不敢把这事提及。
雯青告诉她今天外部又来招呼,说明日七点钟在沙老顿布士宫觐见,他们打发宫车来接。当晚彩云绝早就睡,只是心里有事,终夜不曾安眠。刚要睡着,却被雯青唤醒,说宫车已到,催着彩云洗梳打扮,按品大装。六点钟动身,七点钟就到了那宫前。那宫却在一座森林里面,清幽静肃,壮丽森严,警兵罗列,官员络绎。彩云一到,迎面就见一座六角的文石台,台上立着个骑马英雄的大石象,中央一条很长的甬道,两面石栏,栏外植着整整齐齐高的塔形低的钟形的常绿树。从那甬道一层高似一层,一直到大殿,殿前一排十二座穹形窗,中间是凸出的圆形屋。彩云走近圆屋,早有接引大臣把彩云引上殿来。却见德皇峨冠华服,南面坐着,两旁拥护剑佩铿锵的勋戚大臣,气象很是堂皇。彩云随着接引官走上前去,恭恭敬敬行了鞠躬大礼,照着向来觐见的仪节,都按次行了。那德皇忽含笑地向着彩云道:“贵夫人昨朝辛苦了。”说着,手中擎着个锦匣,说道:“这是皇后赐给贵夫人的。今天皇后有事,不能再与贵夫人把晤,留着这个算纪念吧!”一面说着,一面就递了下来。彩云茫然不解,又不好动问,只得胡里胡涂地接了。这当儿,就有大臣启奏别事,彩云只得慢慢退了下来。
到得车中,轮蹄转动,要紧把那锦匣打开一看,不觉大大吃惊。原来这匣内并非珠宝,也非财帛,倒是一张活灵活现的小影:两个羽帽迎风、长裙窣地的妇人,一个是袅袅婷婷的女郎,一个是庄严璀璨的贵妇。那女郎,不用说是自己的西装小像;这个贵妇,就是昨天并肩拍照的维亚太太。心中恍然大悟道:“原来维亚太太就是联邦帝国大皇帝飞蝶丽皇后,世界雄主英女皇维多利亚的长女,维多利亚第二嗄!怪不得她说,她的身分地位能拘束我了。亏我相处了半月有零,到今朝才明白,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。”心中就一惊一喜,七上八落起来。
那车子却已回到了自己门口,却又看见门口停着一辆轿车。彩云这两天遇着多少奇怪事情,心里真弄得恍恍惚惚、提心吊胆的,见了此车,心里又疑心道:“这车不知又是谁的了。”此时丫鬟仆妇已候在门口,都来搀扶,阿福也来车前站着。彩云就问道:“老爷那里有什么客?”阿福道:“就是毕叶先生。”彩云所了,心里触动昨天拍照的事情,就大喜道:“原来就是他?我正要见他哩!你们搀我到客厅上去。”说着,就曲折行来。刚走到厅门口,彩云望里一张,只见满桌子摊着一方一方的画图,雯青正弯着腰在那里细细赏玩,毕叶却站在桌旁。彩云就叫“且不要声张,让我听听那东西和老爷说什么。”只听雯青道:“这图上红色的界线,就是国界吗?”毕叶道:“是的。”雯青道:“这界线准不准呢?”毕叶道:“这地图的可贵,就在这上头。画这图的人是个地学名家,又是奉着政府的命令画的,哪有不准之理!”雯青道:“既是政府的东西,他怎么能卖掉呢?”毕叶道:“这是当时的稿本。清本已被政府收藏国库,秘密万分,却不晓留着这稿子在外。这人如今穷了,流落在这里,所以肯实。”雯青道:“但是要一千金镑,未免太贵了。”毕叶道:“他说,他卖掉这个,对着本国政府,担了泄漏秘密的罪,一千镑价值还是不得已呢!我看大人得了此图,大可重新把它好好的翻印,送呈贵国政府,这整理疆界的功劳是不小哩,何在这点儿小费呢!”彩云听到这里,心里想:“好呀,这东西倒瞒着我,又来弄老爷的钱了。我可不放他!”想着,把帘子一掀,就飘然地走了进去。正是:
羡煞紫云傍霄汉,全凭红线界华戎。
不知彩云见了毕叶问他什么话来,且听下回分解。